| 全球失衡原因:基于“恒久收入一生命周期假说”与国际分工的视角 |
| 姜凌,王晓辉 2011-03-07 |
| 摘 要: |
本文探讨与整合了导致全球失衡的两种重要微观机制:“巨久收入一生命周期假说”与国际分工理论,并采用最小二乘虚拟变量计量模型(LSDV),利用31个国家1980-2008年相关指标的年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肯定了借贷约束、股市发展、人口年龄结构、医疗福利以及工业增加值等因素对经常账户不同方向与力度的影响。这意味着,全球失衡一方面依旧可用传统的“恒久收入一生命周期假说”视角来解释,缓解全球储蓄过剩与全球失衡的治理措施应该从相关微观机制着手;另一方面,该结论说明全球失衡也是国际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的结果,各国工业化的差异和演进体现了比较优势原则,全球失衡是全球化时代不可规避的必然现象。 |
| 关键词: |
全球失衡,借贷约束,人口年龄结构 ,国际分工 |
|
|
引言
最近十多年,全球失衡(global imbalances)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世界经济现象。其主要特点为美英澳等国经常账户的持续赤字而中国等亚洲新兴市场经济、日德等传统制造业强国、石油产出国的经常账户长期盈余。相关数据显示,尽管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显现,但其规模一直保持在比较稳定的水平。其赤字规模逐年扩大是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的事情,而且是目前经常账户赤字规模最大的国家,占全球经常账户赤字额的65%。与之相对应,亚洲新兴国家的经常账户盈余规模也是此危机发生之后不断增加。石油产出国经常账户长期盈余是石油价格上升导致石油销售收入增加的结果。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其情况比较特殊。虽然“广场协议”后的日元持续升值以及随即而来的资产泡沫破灭,使得该国陷入长期的流动性陷阱、投资的委靡和人口结构的少子化、老龄化也使之储蓄率由1990年的34%逐年下降2007年的28%。但由于其国内不断进步的劳动生产率,其经常账户盈余的历史依旧维持了二三十年。比如,2000年该国经常账户盈余占GDP比重由为2.56%.之后逐步上升到2007年的4.82%。
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一国的经常账户余额等于其储蓄投资缺口,即,CA=S-I。因此,一国外部的经常账户盈余(赤字)必然与一国内部的高储蓄(低储蓄)相联系。中国等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在亚洲金融危机后高储蓄、低消费模式与经常账户持续盈余相对应,美英等发达国家的高消费、低储蓄模式与其经常账户长期赤字相联系。前者高储蓄、低消费的行为模式导致了全球储蓄过剩(global saving glut),进而为美国的长期巨额贸易赤字提供了融资服务(Bernanke,2005),并压低了美国利率水平。
导致一国内部储蓄投资失衡的因素似乎足以解释其外部失衡。的确,目前已经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文献通过解释储蓄或(和)投资来研究全球失衡问题。另外,已经有中国学者(徐建炜和姚洋.2010)独辟蹊径地从国际分工角度直接解释了全球失衡。前种思路侧重于通过解释储蓄投资来研究全球失衡问题的文献,其微观经济学基础其实为“恒久收入一生命周期假说”。他们认为各国在信贷约束、股市规模、人口年龄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各国储蓄率、投资率的差异,进而各国经常账户模式也存在差异,全球失衡因此产生。然而,此类文献的实证模型并没有将上述主要影响因素整合,有的只强调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有的只强调金融发展,并且,其实证模型大多只满足于直接解释储蓄率或(和)投资率,而没有考虑将上述决定因素直接用于解释经常账户余额的变化,后种思路则从国际分工角度进行了实证研究,强调各国在金融业、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差异导致了经常账户盈余率的差异,但是该研究又忽视了前种思路中信贷约束、股市财富效应的重要影响,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而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就在于吸收与融合了“恒久收入一生命周期假说”与国际分工两个研究视角的思路,实证研究采用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方法(LSDV),使用31个国家1980-2008年间的数据,检验了上述视角下相关指标对经常账户盈余率的影响。文章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详细阐述了这两种全球失衡机制.并回顾了相关研究文献。第四部分是计量模型的设定、解释变量说明以及对回归结果的分析。文章第五部分给出了对中国的启示和建议。
图1:各经济体经常账户余额占世界GDP比重:1990-200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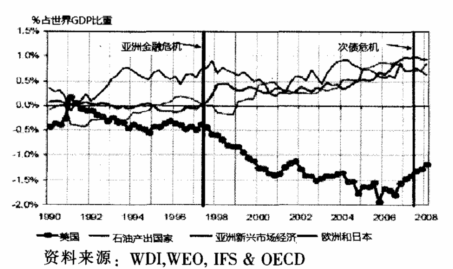
一、 “恒久收入一生命周期假说”视角的全球失衡机制
“恒久收入一生命周期假说”探讨了影响个体消费和储蓄决策的原因.宏观加总意义上的一国经常账户余额最终受之影响。
(一) “恒久收入一生命周期假说”与全球失衡的内在逻辑联系
1.借贷约束导致预防性储蓄增加和经常账户盈余增加
“恒久收入一生命周期假说”认为个体消费与之预期恒久收入正相关,这暗含着个体可通过信贷市场的借贷来跨时期与跨状态平滑消费的假定。然而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居民和企业均面临各种各样的借贷约束,预防性储蓄或因此而居高不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和过去三十年的中国都曾有过高增长低利率下的“高储蓄之谜”。华盛顿大学的Wen (2009)认为借贷约束正是解释此谜题的利器:借贷约束和收入不确定问题的存在迫使居民选择高储蓄,此种预防性储蓄使得边际消费倾向与恒久收入呈现负相关关系。实证研究中,“一国对私人部门的信贷规模占GDP比重”可以很好地衡量一国融资便利程度或信贷的可获得性。该指标值高的国家,意味着居民和企业可以方便地通过银行部门借贷以解决平滑消费和投资需求问题,国内储蓄率与经常账户盈余率或因此减少。
2.股市规模扩大产生财富效应和经常账户盈余减少
“恒久收入一生命周期假说”强调消费取决于预期的终生劳动收入和财产收入。股票、房产等资产价格的上涨使大众名义财富价值增加.因此有可能带来正“财富效应”,进而刺激居民消费、企业投资与商品进口,一国的储蓄率和经常账户余额或因此减少。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就曾指出,美国股市在90年代上涨产生的“财富效应”造成美国消费者支出更多,从而推动了90年代的经济增长:而美国股市2000年网络股泡沫破灭带来的负“财富效应”减缓了消费开支增长。从全球经济整体来看,美联储现任主席伯南克(2005)也强调资产价格变化是连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贸易盈余与发达国家贸易赤字的重要机制之一:美国股市与房市“财富效应”的产生以及低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使国民增加消费和进口而降低储蓄。一般的研究文献多用“一国年度股市市值占GDP比重”、“一国年度股市交易值占GDP比重”来衡量该国股市发展程度。
3.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导致负储蓄和经常账户盈余减少
生命周期假说认为,当人们处于工作年龄时候,人们为了自己的退休生涯而储蓄,当人们退休之后,消费超过收入,进入负储蓄状态。因此,如果一国年轻的劳动力丰富,工作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较大,劳动力的储蓄将超过年老者的负储蓄,一国总储蓄率比较高。相反,如果一国总人口中老年人所占比重较大,老龄化问题比较突出,年轻的劳动力供给相对不足,总储蓄率较低,经常账户盈余率减少问题与容易出现。一般的实证研究文献中,多用一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65岁以上人口占14-64岁人口的比重等指标来测度一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后者就是所谓的老年抚养比(old-age dependencyrate)。
4.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导致预防性储蓄增加
Kotlikoff(1988)生命周期模型中的模拟结果最早表明.社会保障体系“安全网”的建立和健全有助于减少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巨额支出,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迫使居民增加预防性储蓄以针对教育、医疗、养老等事宜进行自我保险(self-insure)。杨汝岱和陈斌开(2009)也在生命周期模型框架下,引入教育支出,用数值模拟方法考察高等教育改革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从理论上探讨其对降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内在微观作用机制。
(二) “恒久收入一生命周期假说”与全球失衡关系的实证研究
关于股市发展对经常账户影响的实证研究,Marcel等人(2007)曾使用1974-2005年期间的季度数据.采用贝叶斯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Bayesian Structural Vector Autoregres-sion),最终脉冲响应模型证实,美国股票市场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10个百分点的上涨,将使美国经常账户余额占GDP比重下降大约0.9个百分点。
关于信贷约束和股市发展对全球失衡的影响.Ito和Chinn(2007)为重点从信贷市场和股票市场综合角度解释全球失衡,使用19个工业国家和70个发展中国家1986-2005年间的数据,其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私人部门信贷和股市市值等反映金融市场规模的指标是储蓄、投资以及经常账户变化的重要决定因素.工业国家金融市场规模的扩大降低了经常账户收支,而在包括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其金融发展程度的进步则提高了其储蓄率,但这与“全球储蓄过剩假设”不一致,该假说认为金融市场发展程度的提高能减少预防性储蓄。另外,该结果也与Gianluigi和Cesar (2007)以及Terrones和Cardarelli (2005)的实证研究结论刚好相反,并完全忽视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
关于人口年龄结构对经常账户的影响,Higgins (1998)最早用10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最早验证了人口年龄结构对经常账户盈余率的影响。其结果表明,30-34岁以后到60-64岁以前.人口占比的增加倾向于使经常账户向顺差方向变动。65-69岁以后,人口占比增加使经常账户向逆差方向变动,且越高年龄段人口的增加越会使经常账户向逆差方向变动。不过该研究没有涉及当前的全球失衡问题。Bosworth和Chodorow (2007)从人口年龄结构角度研究了全球失衡的原因。他们使用85个国家1960~2004年数据.其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收入、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和投资率的确存在着非常强的相关关系。不过,此种关系在亚洲的非工业化国家更为强烈,而在高收入国家较为弱化。作者还预测到,众多老龄化的工业化国家最终还是会步入经常账户赤字状态.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已经为高收入国家的储蓄率下降施加了一个压力。然而,此类研究又完全忽视了金融发展的影响。
关于信贷约束、人口年龄结构两因素对全球失衡的联合影响.IMF的Terrones和Car-darelli(2005)使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和动态因子模型,检验了1972-2004年间46个国家储蓄率与投资率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这46个国家包括21个工业国家、25个新兴市场国家。回归结果发现,高的产出增长增加储蓄率,而对私人部门信贷占GDP比重的提高和老年抚养比的增加都会减少了储蓄率。中国学者何志强( 2007)也曾以此计量模型为框架,发现东南亚地区、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和中国在经常账户盈余影响因素方面的差异性大于共同性。
关于信贷约束、股市发展、人口年龄结构三因素对全球失衡的联合影响.欧洲中央银行的Gianluigi和Cesar (2007)使用面板误差修正模型(panel error correction model)单纯研究了1980-2005年48个国家私人储蓄率的决定因素及其与全球失衡的关系。其中的私人储蓄为家庭储蓄和公司储蓄.48个国家包括26个新兴市场经济体和22个高收入国家。回归结果表明老年抚养比下降的人口结构变化效应,以及对私人部门信贷和股市市值占GDP比重上升的金融追赶效应(financialcatching - up),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储蓄率下降的两种重要驱动力:而高收入国家对私人部门信贷比重的提高却导致私人储蓄率的些许提高。他们最终预测未来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将很可能降低很多国家的储蓄率.未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深化也会有利于国际储蓄的重新配置和平滑调整全球经常账户失衡。
从人口年龄结构和金融发展程度角度出发,亚洲开发银行的Park和Shin (2009)为寻求亚洲金融危机后.导致该地区经常账户长期大量盈余的储蓄过度与投资不足的决定因素,使用面板模型分别对1965 -2004年间包括12个亚洲国家在内的全球137个国家(地区)的储蓄模型和全球141个国家(地区)的投资模型分别进行了固定效应的回归。考虑国别(地区)效应的回归结果表明,老年抚养比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全部国家储蓄率,人均收入、人均收入平方、预期寿命和青年抚养比(一国15岁以下人口与15~64岁人口的比值)也显著影响亚洲国家储蓄率,但是以“一国M,与GDP比值”来衡量的金融发展程度指标对储蓄率的负向影响是不显著。另外.为关注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当引入关于时间和亚洲危机国家的两种虚拟变量后,随机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显著的过度预防性储蓄问题和投资不足问题.而危机前该地区存在着的投资过度问题转化为危机后投资不足问题。
不过,前述实际基于恒久收入一生命周期假说视角的实证研究没有考虑信贷约束、股市规模、人口结构对经常账户余额的直接定性影响,也没有意识到国际产业转移、国际分工对全球失衡的贡献。
另外,关于社会保障体系与全球失衡,目前还没有相关的实证研究文献。不过,已有一些实证文献研究了该因素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Diamond和Hausman (1984)使用个体数据的估计结果表明.社会保障投入每一美元的增加对应着储蓄45美分的减少。以医疗福利和全民医疗保险为例.Gruber和Yelowitz( 1999)曾发现美国的联邦医疗补助项目①1984~1993年间的扩张使得低收入人群1993年的储蓄率下降了17.7%、消费增加了5.2%。Chou等人(2003)也发现中国台湾省的全民健康保险(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使岛内居民预防性储蓄下降8.6%-13.7%。
二、国际分工视角的全球失衡机制
国际分工产生与维持的原因在于,全球化时代的各国可以更为充分地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由此产生的国际产业转移使各国在全球分工链条上处于不同的环节.经常账户盈余的国别差异自然产生。
(一)国际分工与全球失衡的内在逻辑联系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与国际分工模式的深化.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已经实现将本国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传统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到劳动成本低廉的中国等亚洲发展中国家。全球制造业中心(真实财富创造中心)和货币金融中心出现了分离。
英美等国长期的国际产业转移使其国内出现了“产业空心化”.重点转向作为其比较优势的金融业等虚拟经济以及第三产业(张燕生等,2010),而日德等传统制造业大国实现了将低附加值生产环节向亚洲地区的国际转移.自身的优势转向高端消费品和高附加值制造品上.中国等新兴制造业国家则处于全球务工体系与价值链条的低端(徐建炜和姚洋,2010)。此种国际分工模式下,日德以及中国等亚洲发展中国家对英美等国的商品出口需求依赖度增强,前者经常账户走向盈余与后者经常账户走向赤字的全球失衡格局不可避免。
(二)国际分工和全球失衡关系的实证研究
基于上述类似的逻辑.徐建炜和姚洋( 2010)从国际分工的角度考察了全球失衡问题。他们认为当今世界的分工格局是,在实体经济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日本、德国、中国等国和石油输出国)出口货物,因而拥有大量的经常账户盈余.而在虚拟经济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主要是美国和英国)出口金融服务,因此拥有大量的经常账户赤字。通过构造一个金融市场一制造业比较优势指标.并利用1990-2006年的40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系统的计量研究.结果证实了金融一制造业比较优势对于经常账户赤字(盈余)的重要性。但遗憾的是,该研究尽管也考虑和肯定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但却忽视了信贷约束、股市财富效应等重要微观机制对经常账户盈余率的影响。
三、计量经济学建模与分析
(一)计量模型设立
本文的实证研究思路整合了基于“恒久收入一生命周期假说”以及国际分工理论两种视角下的全球失衡机制。除了重点关注上述信贷约束、股市规模、人口年龄结构传统解释变量对经常账户盈余率的直接影响,并引入了能够反映国际产业转移与国际分工的各国工业化程度指标、反映社会保障体系的医疗福利等指标。
本文所用计量经济学模型为考虑了国别效应与时间效应的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方法.( LSDV),该方法是估计面板模型固定效应的一种方法。所用数据为31个国家1980~2008年相关指标的年度数据。这31个国家包括24个OECD国家以及7个亚洲发展中国家。24个OECD国家有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韩国、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新加坡、西班牙、瑞典、英国、美国,7个亚洲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印尼、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文中所用指标的原始数据均取自世界银行的World DevelopmentIndicators (WDI)数据库。
本文中计量模型的具体设置形式为:
Y=C+Xβ+Dα+Tγ+ε
因变量v为一国经常账户盈余率,亦即经常账户余额占GDP比重。X为各解释变量,D为表示国别效应的虚拟变量.T为表示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年份的时间虚拟变量。各解释变量包括: (1)人均GDP及其平方, (2)对私人部门信贷占GDP比重, (3)股市市值占GDP比重, (4)老年抚养比, (5) 医疗福利虚拟变量. (6)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7)贸易条件。
其中, “恒久收入一生命周期假说”框架下的全球失衡机制,体现在对私人部门信贷占GDP比重、股市市值占GDP比重、老年抚养比和医疗福利虚拟变量对经常账户盈余率的影响方向和力度上。而国际分工框架下的全球失衡机制体现为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对经常账户盈余率的影响。本文预期,对私人部门信贷占GDP比重、股市市值占GDP比重、老年抚养比和医疗福利虚拟变量等指标将负向影响经常账户盈余率,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将正向影响该指标。另外,人均GDP对该指标的影响将呈现倒U型关系。
(二)主要解释变量说明
1.人均GDP及其平方
人均GDP可表示一国经济发展阶段。而经济发展阶段是决定储蓄率以及经常账户余额的最为关键因素。罗斯托曾在《经济增长阶段》一书中指出,起飞阶段国家的储蓄率会随着人均收入增加而增加,储蓄率水平较高:大众高消费阶段国家的储蓄率会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储蓄率保持在15%N22%之间:成熟阶段国家的人均收入和储蓄率不相关.人均收入增加,但储蓄率始终在30%-40%之间徘徊。基于此考虑,本文预期人均GDP对经常账户盈余率的影响将呈现倒U型关系。
2.对私人部门信贷占GDP比重
对私人部门的信贷规模( domestic creditto private sector)占GDP比重能衡量一国融资便利程度或借贷约束。一国该指标值越低,意味着借贷约束将会使该国预防性储蓄较多、消费较低,其经常账户也有可能因此保持长期顺差状态。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荷兰、香港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该指标1997-2008年的平均值多在1100/0-180%之间,而印度、印尼、菲律宾、巴基斯坦、越南等国该指标1997-2008年的平均值多为30qo左右。
3.股市市值占GDP比重
股市市值(market capitalization of listedcompanies)占GDP的比重衡量了一国股市规模或发展程度。如果该指标值长期保持高位或处于增长态势,则有可能带来财富效应以及经常账户余额相应地减少。WDI只提供了该指标1988年后的数值,中国该指标值更是1991年后才有。从该指标具体数值来看,美国、英国、新加坡1988-2008年间该指标的平坞值分别为111%、126%、163 010,而德国、日本的分别为38%、83%,这与亚洲发展中国家40%左右的水平差不多,这反映了日德以银行主导的金融系统结构特点。
4.老年抚养比
老年抚养比为一国“65岁以上人口与15-64岁人口的比率”,亦即一国非劳动年龄人口的老年部分与劳动年龄人口数的比值,用以表示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老年人。OECD大多数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已经呈现出老龄化特征。2008年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瑞典、比利时、丹麦、芬兰该指标值介于0.24 -0.26之间,日本、德国、意大利更是高达0.33、0.30、0.31。不过,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比较特殊.1980-2008年,该指标值多稳定维持在0.18左右的水平,这或许是因为移民迁入使之国内老年抚养几十年都比较稳定。亚洲发展中国家人口年龄结构总体都比较年轻,2008年中国、印度、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巴基斯坦、泰国等国该指标值均介于0.07-0.11之间。
5.医疗福利虚拟变量
一国“全部医疗开支中公共医疗开支所占比重” ( public health expenditure of totalhealth expenditure)可以近似地衡量其国内医疗福利状况和社会保障体系。本文中,由于WDI中所有国家该指标数据只有2003-2004年有.因此本文先逐个计算出31个国家该指标的四年平均值,然后再计算出31个国家该指标跨国均值64,36%。当一国“每年全部医疗开支中公共医疗开支所占比重”超过64.36%时.则医疗福利虚拟变量设置为1,表示该国医疗福利水平高,否则为O,表示该国医疗福利水平低。
表1:主要国家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阶段性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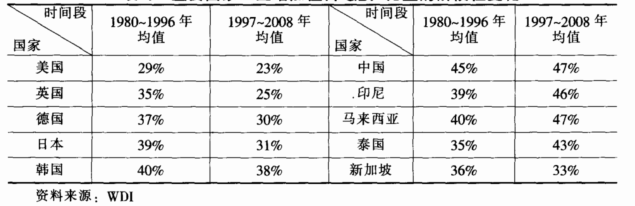
OECD国家多为高福利国家.其中的欧洲各国以及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全部医疗开支中公共医疗开支所占比重”均在70%以上。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实现全民医保的国家,其指标值仅为45%。而亚洲国家该指标更小,中国、印尼、马来西亚只有40qo,印度和巴基斯坦更是只有25%。另外,新加坡、韩国也只有30%多和500/0的水平。
6.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全球化时代,一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 (industry value added as percentageof GDP)可以衡量其国内工业化水平与产业结构。英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在七十年代就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张燕生,2007),如表l所示.其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八十年代都比较低.而且在九十年代中后期都还有所下降。尽管如此,由于发达国家日本与德国由于处于国际生产网络的高端.该指标值第二个时期虽然有所下降.但也保持在31%和30%的水平,而美国和英国产业空心化问题严重,该指标分别降低到为25%和23%。中国、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亚洲发展中国家由于本身还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加之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该指标在八十年代就比较高,九十年代中后期更是上升到45%的水平。另外,作为亚洲“四小龙”成员的韩国和新加坡.该指标值在九十年代中后期也分别保持在38%和33 010的水平。从国际分工对全球失衡影响的逻辑考虑.本文预期“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较低的国家容易走向经常账户赤字。
7.贸易条件
贸易条件改善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是模棱两可的。如果贸易条件与储蓄率正相关,意味着经济主体认为正的贸易条件冲击不过是一种暂时性的正向收入冲击,因此提高储蓄率,这叫做“Harberger -Laursen - Metzler”效应,经常账户因此也会处于盈余状态。本文中贸易条件利用WDI提供的相关指标计算而来。具体计算方法为:贸易条件=(出口价值指数/出口数量指数),(进口价值指数/进口数量指数)。
(三)回归结果分析
模型(1)至(5)的回归都考虑了国别效应和亚洲金融危机时间效应。模型(1)主要关注经济发展水平、私人信贷和人口年龄结构等指标对经常账户的影响。模型(2)加入了股市市值。模型(3)加入了医疗福利虚拟变量。模型(5)加入了工业增加值。其中,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与私人信贷、股市发展、人口年龄结构、医疗福利、产业结构的相关度比较高,模型(4)和(5)剔除了经济发展指标人均GDP及其平方。最终,各个模型的回归结果验证了我们之前的猜测。具体的:
模型(1)中,反映经济发展程度的人均产出与经常账户盈余率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高收入的国家经常账户盈余容易减少或走向赤字状态.而低收入国家则容易处于经常账户盈余状态。这与现实情况非常符合,也意味着罗斯托关于经济发展阶段与储蓄率关系的论述也适用于诠释当前的全球失衡。
模型(1)至(5)中,对私人部门信贷占GDP比重1个百分点的提高,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将导致一国经常账户盈余率0.04-0.06个百分点的下降。这意味着,信贷可获得性的提高,有助于减少居民预防性储蓄和企业内部积累,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的增加降低经常账户盈余率。
模型(1)至(5)中,股市市值占GDP比重1个百分点的提高,在5010的显著性水平上,可导致一国经常账户余额占GDP比重0.017-0.018个百分点的下降。这间接表明股市发展带来的财富效应增加了消费和投资需求,经常账户盈余率进而减少。
模型(1)至(4)中,老年抚养比率1个百分点的提高,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可导致经常账户余额占GDP比重0.33 -0.42个百分点的下降。可见,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的确是经常账户盈余率减少的一个重要因素。
模型(1)至(4)中,医疗福利虚拟变量取值为1的国家,在5 010的显著性水平上.其经常账户盈余率比该比值虚拟变量为零的国家低4.46个百分点。这反映了良好的医疗福利制度有助于刺激消费、减少储蓄、降低经常账户盈余。
模型(2)中,贸易条件改善增加了经常账户盈余,虽然此种关系在其他四个回归模型中不全显著,但也间接验证了“Harberger -Laursen- Metzler“效应的存在和预防性储蓄行为作用。
模型(5)考察了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对经常账户盈余率的影响,这体现了国际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格局下各国产业结构差异和全球经常账户失衡的内在联系。由于该指标与人均GDP负相关,模型(5)中的解释变量因此排除了人均GDP及其平方。其回归结果显示,一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1个百分点的上升,将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导致经常账户余额占GDP比重0.497个百分点的增
表2:所有经常账户余额模型(LSDV): 1980-200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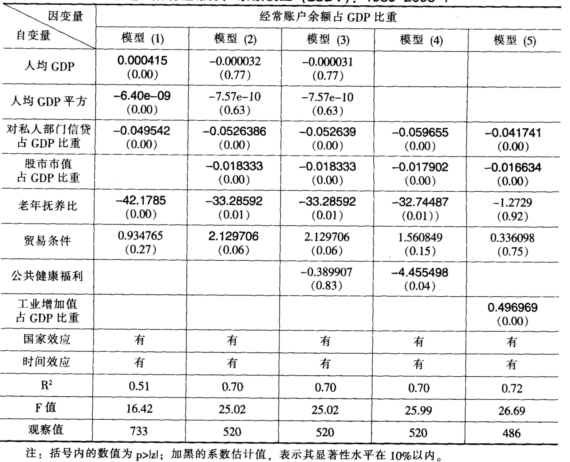
加。此模型中,对私人部门信贷和股市市值对经常账户的负向影响依旧显著,只不过影响力度稍有下降。而老年抚养比对经常账户的负向影响变得不显著度,这主要是因为老年抚养比和工业化指标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即人口年龄结构偏老的多为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由于国际产业转移.国内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较低。总之,模型(5)证实了国际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格局下各国产业结构差异成为全球失衡的重要决定因素。这与徐建炜和姚洋( 2010)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尽管他们的实证研究忽视了信贷约束、股市财富效应对经常账户盈余的影响。
(四)实证研究不足
由于受制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实证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 (1)医疗福利指标的计算仅仅是以2003-2007年的数据为基础,不能概括考察的所有国家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医疗福利.更不能反映一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程度。 (2)反映资本市场发展的指标选择上.没有考虑房地产市场房价变化及相应的财富效应对经常账户动态的影响。不过,由于股市与房地产市场联系比较紧密.股市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也反映了房市的发展。
四、“恒久收入一生命周期假说”和国际分工视角下的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分析
我国经常账户长期盈余和高储蓄率现象也完全可以在“恒久收入一生命周期假说”以及国际分工两种解释全球失衡的框架下来解释。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开看:
(一)从金融发展来看,我国的金融结构主要由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股票市场构成。此种垄断性金融结构一方面导致银行系统呆账坏账多、股市投机气氛浓厚,股市财富效应难以实现.另一方面导致富有效率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银行融资成本高、上市融资门槛高,家庭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因此都比较高。与此同时,我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尚未建立,股市、债市、产业基金发展力度远远不够,居民与企业缺乏长期投资渠道与工具。2004-2005年,居民资产的72%为银行存款:企业外部融资的主要方式是银行贷款而非股市融资(Yi和Song,2008)。
(二)从人口年龄结构看,祝丹涛( 2008)曾指出我国经常账户的长期盈余其实是我国在“人口红利”期于海外储蓄养老金的结果,是年轻的中国为应对15-20年后的“养老”而在海外积攒的储蓄:但从2020年左右到2030年.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将使我国“人口红利”将消失,储蓄率与经常账户盈余率将下降。
(三)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我国政府尚未实现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职能的转换,长期的生产性财政模式重视对生产性项目的投资,而对教育、卫生、社会保障领域投资不足(张燕生等,2010)。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使城乡居民面临医疗、教育、购房、养老等尖锐问题考验。预防性储蓄由此居高不下。
(四)国际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我国是整个东亚国际生产网络的最末端组成部分,其贸易顺差额主要由外商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品出口造成。经常账户长期盈余是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参与国际分工的必然结果。
可见.解释与解决中国的高储蓄和经常账户持续盈余问题完全可以从信贷约束、股市发展、人口年龄结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国际产业转移等结构性因素考虑释,而不应该只是从宏观经济学层面争论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大力发展信贷市场、提高股市效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调整计生政策、鼓励中国创造、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才会让中国对全球失衡和全球储蓄过剩的调整作出自己的贡献。
五、结论
以“恒久收入一生命周期假说”为基础来理解全球失衡机制,注重探究各国在信贷市场与股票市场的发展程度、人口年龄结构、社保体系建设程度等方面的差异与经常账户盈余的差异。除此之外,比较优势原则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依旧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各国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国际产业转移背景下各国工业化进程与产业结构的差异也应该成为影响全球失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本文采用最小二乘虚拟变量计量模型证实了信贷市场、股市发展、人口年龄结构、医疗福利以及国际产业转移等结构性因素对经常账户的重要影响力。这表明,全球失衡的部分原因依旧可从传统的“恒久收入一生命周期假说”视角来解释,缓解全球失衡应该从国内相关微观机制着手:另一方面,全球失衡同时也是国际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的结果,各国工业化的差异和演进体现了比较优势原则,全球失衡是全球化时代不可规避的问题。
|
|
|

